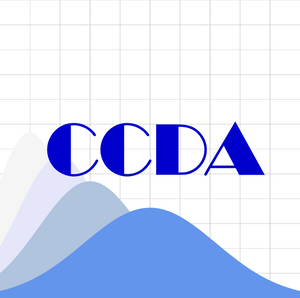CCDA评论 | 唐世平:我的现代化情结
前言
1. 起因
我成长在“四个现代化”的年代。事实上,从我开始懂事起,就一直在体验和参与中国的(以及世界的)现代化(或者还没有完成的现代化),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我们这一届(1981)是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届读完正规的初中和高中(1977-1981)的大学生。当时的我天真幼稚地认为,中国只需要有现代化的科学就能实现现代化了。【周恩来总理提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完全技术化的: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显然,这几个现代化几乎都必须基于“科技现代化”。】因此,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自然)科学”,而且发自内心地鄙视“文科”。因为不会填志愿,我于1981年阴差阳错地到中国地质大学(原“武汉地质学院”)就读。尽管没有学到我最喜欢的专业(生物学),但是在中国地大的四年,我确实是“开了眼界”。因为学期中和每一个暑假都要到不同的地方实习,我大学期间去过中国的6个省市(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北京、陕西)。【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上地质学院其实非常“划算”的,因为它给了我多次看中国的机会。1982年暑假,我们第一次去实习,在郑州转车,在车站广场上我和好几位同学都被骗过几元钱。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社会课吧。】平心而论,那个年代,我们所到之处都是非常贫穷的,即便是北京。而最后的毕业实习的1984年,更是在陕西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的西口镇待了四个月。期间,我们见识了当地百姓的朴素、农村青年对上大学的渴望,以及让我深感震惊的贫困【我一直说,“贫穷”和“贫困”非常不同】。1985年,我通过自学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终于学上我真正喜欢的生物学。1988年我从中国科技大学拿到生物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加入了中国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华美生物工程公司”(它已经不存在)。作为洛阳肉联厂(之后的“春都集团”)和美国普罗麦格(Promega)公司的合资公司,公司坐落在古都洛阳。1988~1989年,我还带着我的好几位同事又去了一趟秦岭深处。此外,我也到过豫北的三门峡、南阳等地。总体来说,我已经能够感受到神州大地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但总体还是非常贫穷的。1989~1990年,通过各种努力弄到了一个“特区证”,我来到深圳特区工作。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所迸发的活力,这和内地的风景几乎是天壤之别。1990年上半年,我们还通过香港电视的现场直播看到了苏东巨变:外面的世界也正在发生巨变。同样是因为阴差阳错,1990我来到位于底特律市的Wayne State University留学,继续攻读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临行前,我父亲叮嘱我说,将来一定要回国啊。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会回国,因为我从小就爱我的乡亲和人民:我的爱国是极其朴素的。1990年的底特律市并不是美国最好的城市,甚至可能是当时美国最差的城市之一。整个市中心十分败落,白人和有钱人都住在郊区。这也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种族歧视。但平心而论,即便是当时的深圳的发展水平,也离底特律的发展水平有巨大的差距。这期间,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体会。一是我在中国科大培养细胞,无论我怎么在所谓的“无菌间”仔细操作,细胞都一定会在基本不超过一个星期就被污染。【我曾经为此几乎绝望。】而在美国的实验室培养细胞,我其实都不用无菌间,就是一个无菌操作台,然后细胞也长得很好。二是我1986年在上海中科院有机所做有机合成时,几乎所有标着99.9%“实验室纯”的国产基础试剂(比如乙醇、乙醚等),都是需要自己先纯化一遍才能用。而在美国的实验室,所有的试剂都是直接就可以用。1995年我来到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做博士后。圣地亚哥和墨西哥的蒂华纳(也译成“提瓦那”,Tijuana)市接壤,而且从美国过去可以不需要签证,因为我就决定去看看。我天真的以为,蒂华纳和圣地亚哥就像深圳和香港,因此,我想蒂华纳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城市。结果,我发现我是彻底错了。首先,蒂华纳的公共汽车和我老家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小县城的公共汽车几乎一样的破旧。而我去的那个街区,一到傍晚就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吓得我赶紧打道回府。当时的我,几乎不敢相信,蒂华纳居然不像深圳!1997年初,第一次回国探亲,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后20年的神州大地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也让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强的信心。但是,我老家的农村其实还是非常贫穷,甚至还是“贫困”的。1997年再次回到美国后,我转入了社会科学。不过当时的我其实对社会科学也没有太多的概念。1999年我拿了一个社会科学的硕士学位后,终于回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工作。2002~2003年,我作为“西部博士服务团”的一员,被分配到宁夏外经贸厅挂职锻炼。期间去了几次被称为联合国认定的“极端贫困地区”的“西海固”地区。这是我第一次领略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其间的“贫困”再次让我震撼。在这期间,我还去印度访问了两周。也许是这些巧合的经历,让我从2002~2003年开始真正认真地思考现代化。
2. 如何思考现代化
现代化是国家发展最为核心和经久不衰的话题。我坚持认为,现代化,或者说“国家的兴衰”仍旧是整个社会科学的终极课题之一(另一个是“冲突与合作”)。我猜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地思考现代化,其原因就在于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并非易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现代化始终是无数仁人志士、贤明领袖和劳苦大众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而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现代化就始终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也正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但是,现代化的成功者寥寥而失败者甚众。我经常把现代化比喻成一座孤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想游上去。但迄今为止,也就只有40个国家左右游上了岛。许多国家还在努力地游,而有些国家或者地区要么抱着一块礁石或是一棵枯树停滞了,要么快要沉下去了。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也还没有完成,“同志还需努力”。那为何现代化成功者寥寥而失败者甚众?要回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需要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功很困难,但解释成功则相对容易;失败很容易,但解释失败却非常困难。显然,我对现代化的一些零星体验并不足以让我很好地思考和研究现代化。在我转入社会科学之前,我曾经断断续续茫无目的读过一些书籍,似乎也是为了能够思考现代化。在大学的时候,估计也是我还是比较幼稚的时候,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我还是看了一点近现代历史,也读过《走向未来》丛书中的几本小册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对我影响深刻,是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 1910-1989)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我个人认为,他的书其实比艾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更加有力量。但因为斯诺走的是上层路线,而贝尔登则是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因此斯诺的名望要远远高于贝尔登。这些书大致就是我的社会科学的启蒙。我是在转到社会科学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因为师从苏俄,1990年前的中国其实是没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的。特别是,我们很长时间都把“哲学”封为指导一切科学,甚至认为“哲学”可以代替“社会科学”。在1990年前,中国最接近社会科学的只有历史学。但是,中国的历史学长期以来也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加上一些东北亚史,甚至东南亚史都不多。【我一直觉得,中国如今的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还是太过关注中国自己的历史,最多只是用了一些更炫的方法而已。相比之下,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经历关注都不太够,除了一部分西方国家和我们的重要邻国之外。因此,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吸收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我呼吁“少读点中国历史”的初衷。】没人能否认现代化是从西欧的边陲开始的。因此,我认为,要想研究现代化,我们还是必须回到现代化的起点,然后慢慢探寻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和展开。现代化覆盖全球的过程,背后当然有西方坚船利炮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驱动,但更大程度上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试图从西方学习,尽快实现现代化而成为富强的国家的驱动。而我对中国在不同现代化阶段的体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的差别的体验(从内地到深圳、从深圳到美国,从美国到中国,从中国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中国),已经把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因此,我大致认定,要想真正研究好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同样要打破“中国中心主义”,要从更加宏阔的时空下来审视现代化的缘起与扩散。
3. 何谓现代化?
现代化既是一个动词(modernize),也是一个(动)名词(modernization)。大致可以说,现代化作为一个动词就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和过程。而现代化作为一个名词,则是对一个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的测量和判定。因此,这就涉及到如何定义和度量现代化(程度)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复杂(困难)”的概念。首先,现代化是一个复杂概念,因为不同的人群、社会、组织对它的理解和认可度都是不同的。比如,可能不少人士对于现代化至少包含一部分世俗化就不一定认可。其次,现代化又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概念”,即具有多个维度,同时具有多个层次的概念。我们认为,现代化有四个大的维度: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我们认为军事现代化主要是政治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综合结果(比如,国家常备军队、装备对战军队的战斗力的贡献越来越大等等)。当然,在书中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会把现代化拆解成为更加细致的维度进行研究。我们没有将“文化”作为一个大的维度。“文化”的变迁当然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要么是其它几个大维度所支撑的结果,要么是属于“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而在社会方面,现代化的最核心体现之一确实是一个思潮或者精神体系,而这个精神体系的核心就是让理性的光辉照耀我们周围的世界,即“觉醒(enlightenment)”。【我个人认为,将“enlightenment”译成“启蒙”其实是差强人意的。】
4. 对于本书的思考
在主体脉络上,我们强调,现代化问题的核心之一当然是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却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们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努力,尽管因为现代化的缘起和早期现代化因为观察数的限制,我们无法用定量的方法做太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突出了对时空下的“因素组合+机制”的解释的强调。更具体的说,按照时空,我们能够将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分成至少三大波现代化,因为这三大波现代化的时空是非常不同的。而每一大波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小波。当然,我们的努力是建立在前人的努力之上的:我们既吸收西方和其它国家的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吸收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并不认为,非西方就一定是“东方”,而可以是其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思考。此前“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的研究的核心谬误是,因为西方是如此现代化的,因此其它非西方国家要赶紧如此才能现代化。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限制:因为非西方国家,甚至西欧和中东欧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在英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阴影下的现代化,因此,它们无法重走英国的道路。而“反西方主义”,或者说是非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则犯了另外一个方向的谬误。他们通常认定,他们必须抵制西方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研究表明,通往现代化的路确实可能不止一条,但也确实没有很多条。因此,西方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包括他们的部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思想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比如,“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或者地区能基于计划经济实现现代化。但是,非西方国家确实没法完全照抄英国的经验。这一方面是因为时空的限制意味着非西方国家不再有英国和西欧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实现现代化之前的非西方国家和实现现代化之前的英国一样:它们都不是白纸一张。因此,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被困在崎岖的历史中,只能“负重前行”。我们深知,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读者们能够觉得,我们的努力不仅有全球视野,也有研究思路和理论方面的创新,并且融合了多种方法(包括我们自己发展的某些方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中国学者来研究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为中国提供更加有用的知识,也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加有用的知识。最后,我想特别强调,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叶成城博士努力的成果。我主要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在少数的几个章节贡献了一点框架和一些粗糙的具体思想。P.S. 关于美国此次大选,我的团队根据ABM模型的结果,认为特朗普获胜的概率很大。
北京时间2024年11月3日上午10点(美国总统大选前两日),唐世平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研究团队正式发布对将于11月5日举行的美国第60届总统选举的预测结果。数据指出,特朗普极有可能再度问鼎美国总统宝座(概率超过60%)。
原文编辑:维维一笑
原文审核:高瓴
注:截至转载推文发布时,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特朗普成功锁定第二任期,这一结果与中心研究团队的预测相符。
唐世平教授简介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唐世平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副主席。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多个领域均有广泛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五部英文专著、三部中文专著、一部英文编著和三部中文编著。其中,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于2015年荣获 ISA “年度最佳著作奖”,是亚洲和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他的第五部英文专著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于202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也是多个国际顶级和一流刊物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编委会成员。
唐世平教授是中国计算社会科学、特别是决策计算的拓荒者之一,他提出了基于“全数据计算”(total data computation)的“决策计算社会科学”理念。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简介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我国第一个基于“计算社会科学”,专门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的研究中心。中心立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前沿,直面变化与复杂的世界,旨在建立起一套基于广泛而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方法的分析框架、模型和工作软件,将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实际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把战略行为和战略决策研究的经验一般化、模型化,做到可复制、可移植。通过改进或整合既有的技术平台,开发新的技术平台,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技术支持中心,为我国的战略分析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中心的成立得到了来自国家多个重要部门和机构的支持。从2016年起,完全抛开民意调查,而是基于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中心的团队已经连续五次精准预测了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中心还开发了多款针对其它复杂决策问题的计算模拟预测平台。